员工乐园
异彩纷呈的及第诗与落第诗
党海政
【谨按:科举是隋唐以来读书人的出身正途,历来为世人所重。因科举考试结果而产生的“及第诗”和“落第诗”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璀璨的奇葩,并由此可窥知当时的世态人心。昔年曾为此写有一篇专文,于2005 年7月23日至8月16日连载于《香港文汇报》副刊。发表时,可能编辑为求通俗,改文章总名为《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科举》,内容也略有删节,并酌加了一些副标题。连载网址如下:
为免翻阅之劳,现将当初的投稿原文照贴如下。】
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”两句耳熟能详的“神童诗”,道出了科举考试最大的戏剧性,也道出了它巨大的吸引力所在。“男儿欲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连皇帝都这么振臂高呼,响应者自然如过江之鲫。然而鱼集龙门之下数千,跃而成龙者不过七十二条,其余都“暴鳃点额龙门下”。得之则喜,失之则痛,不免人之常情。歌以咏言,诗以言志,于是便有了这异彩纷呈的及第诗与落第诗。
(一)
自是嫦娥爱少年
年少初登第,皇都得意回。
禹门三级浪,平地一声雷。
禹门三级浪,平地一声雷。
同是金榜题名,也分三六九等,最妙不过这少年登科,一举成名了。清代褚人获的《坚瓠集》里载有一首《鹧鸪天》,写得更得意:
五百名中第一仙,等闲平步上青天。
绿袍乍着君恩重,黄榜初开御墨鲜。
龙作马,玉为鞭,花如罗绮柳如烟。
时人莫讶登科早,自是嫦娥爱少年!
金汤镀了出长安
但有幸少年登科、“一举而霸”的毕竟是凤毛麟角。唐人有言曰: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,绝大多数应考者都是忍受了几个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煎熬才有幸获取一第的,无怪乎四十六岁的孟郊一旦金榜题名,便显得如此意气风发:
但有幸少年登科、“一举而霸”的毕竟是凤毛麟角。唐人有言曰: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,绝大多数应考者都是忍受了几个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煎熬才有幸获取一第的,无怪乎四十六岁的孟郊一旦金榜题名,便显得如此意气风发:
昔日龌龊不足夸,今朝放荡思无涯。
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
唐僖宗光启三年,那个曾因一首《鹧鸪诗》蜚声诗坛而被人送雅号“郑鹧鸪”的郑谷也金榜题名了,写下过“雨昏青草湖边过,花落黄陵庙里啼”的诗笔,写起登科的感受来也别有一番风味:
春来无处不闲行,楚润相看别有情。
好是五更残酒醒,耳边闻唤状元声。
登科后的孟郊只顾得在繁花似锦的京城里策马狂奔,而郑谷则显得那样从容:先是四处逛逛瞧瞧,然后去温柔乡“平康里”拥花眠柳,而且还喝了不少的酒。
“六年衣破帝城尘,一日天池水脱鳞。”“河中得上龙门去,不叹江湖岁月深。”唐宪宗元和十四年,钱塘人章孝标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中了进士。“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”,而老朋友李绅刚好在扬州做官,一定顺路看看他:
及第全胜十政官,金汤镀了出长安。
马头渐入扬州郭,为报时人洗眼看。
查名需向榜头看
如果说章孝标沾沾自喜的成份要多一些,那么曾鹤龄的诗则在扬眉吐气中还满含揶揄。明永乐十八年,江西泰和人曾鹤龄赴京会试,途中和一些浙江举子同乘一船。那些人年少轻浮,总拿已经有些年纪并且沉默寡言的曾鹤龄取笑,并纷纷讥讽道:“老先生不过是偶然中举罢了。”并送他一个绰号“曾偶然”。曾鹤龄哭笑不得,也无可奈何。岂料等到发榜,曾鹤龄高中状元,而那些嘲笑他的人竟无一人得中。于是曾鹤龄慨然赋诗一首相赠道:
如果说章孝标沾沾自喜的成份要多一些,那么曾鹤龄的诗则在扬眉吐气中还满含揶揄。明永乐十八年,江西泰和人曾鹤龄赴京会试,途中和一些浙江举子同乘一船。那些人年少轻浮,总拿已经有些年纪并且沉默寡言的曾鹤龄取笑,并纷纷讥讽道:“老先生不过是偶然中举罢了。”并送他一个绰号“曾偶然”。曾鹤龄哭笑不得,也无可奈何。岂料等到发榜,曾鹤龄高中状元,而那些嘲笑他的人竟无一人得中。于是曾鹤龄慨然赋诗一首相赠道:
捧领乡荐谒九天,偶然趁得浙江船。
世间固有偶然事,岂意偶然又偶然!
曾鹤龄的揶揄到了杨守勤那里,则一变而为慷慨激昂。明万历三十一年冬,浙江慈溪举人杨守勤赴京会试,路过扬州时已是囊空如洗,便向一位正在当地做县令的昔日同窗告贷。谁知“人一阔脸就变”,这位县太爷不但将杨守勤的名剌退回,还在上面批上语含嘲弄的“查名”二字。饥寒在身的杨守勤只得忍辱北上。岂料数月之后,天旋地转,杨守勤连中了次年的会元与状元。状元及第后的杨守勤立即给那位同窗寄去一首诗:
萧萧行李上长安,此际谁怜范叔寒。
寄语江南贤令尹,查名须向榜头看!
“兄弟我当年落魄江湖,你连一个子儿都不肯借。现在我告诉你这个小小县令,你不是要‘查名’吗?那就请看看黄金榜上的状元郎!”
四百年后我读这首诗,都替杨守勤出一口恶气!
(二)
五十年前二十三
科举考试的荒唐性,就在于他能让蓬门荜户的寒士一直心存侥幸,终其一生都做着突然富贵的梦想,此即所谓“炼尽少年成白首”、“赚得英雄尽白头”。
“白头英雄”们还是大有人在的,唐昭宗天复元年辛酉科,及第进士中曹松、王希羽、刘象、柯崇、郑希颜等五人都已经七十岁上下,故时人称此科为“五老榜”。“五老”中的曹松便是那个写过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著名非战诗句的诗人,看来他对舞刀动枪的“武战”是颇有微词的,但他对科场的“文战”却有着走火入魔般的痴迷,怀抱 “岂能穷到老,未信达无时”的雄心壮志,从年未弱冠一直考到古稀之年,锲而不舍,百折不挠,着实是“一人功成万发白”。
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浪还比一浪高。大唐津津乐道的“五老”,到了大清朝已再难领风骚。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时,应考者黄章已满百岁,入场时特地让曾孙提一盏灯笼在前引路,灯笼上大书四字曰:“百岁观场”,一时耸动京华。山外青山楼外楼,强中更有强中手。到了清乾隆年间,又出了位傲视古今的陆从云,他100岁成秀才,103岁中举人,104岁又豪气干云地赴京会试。科举之迷人,由此可见一斑。
这种“青春做赋,皓首穷经”的例子代不乏人,甚至还有古稀之年发一发少年狂闯入三鼎甲的,如唐代的尹枢、尹极兄弟二人都是七十余岁大魁天下,清代的姜宸英七十岁中了探花。北宋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的故事被写进了蒙学经典《三字经》,士林艳赏,天下传颂,本来引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,不幸却被洪迈考证出来是假的,十分地煞风景。好在范正敏在《遁斋闲览》里替梁灏做了一首及第诗,却不妨照搬来:
天福三年来应试,雍熙二年始成名。
饶他白发镜中满,且喜青云足下生。
观榜更无友朋在,到家唯有子孙迎。
知他年少登科好,争奈龙头属老成。
好一派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景象,俨然是“蒸不烂,煮不熟,捶不扁,炒不爆,响当当一碗铜豌豆”。但既然其事纯属虚妄,诗又由别人代拟,是否真能反映一个八十二岁中状元的老人当时的心情,毕竟可疑,而且还有恰恰相反的例子在。明崇祯年间,名士陈大士中举,时年五十八岁,观榜时,忽然黯然泪下,别人问其原因,陈大士即诵李商隐的诗句道: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终于功成名就了,但韶华已逝,青春不再,我是很理解陈大士当时临榜流泪的心情的。
再如南宋的陈俢。陈俢于宋高宗绍兴八年中探花,时年七十三岁。由于一生都忙于科举,到此时尚未娶妻。宋高宗怜其年老,特地将一名宫女赐予他为妻。时人赋诗道:
读尽诗书五百担,老来始得一青衫。
新人若问郎年几?五十年前二十三!
清人有诗曰:“有酒休辞连夜饮,好花须及少年看。”一生的大好光阴都虚掷浪抛在一次次应试,一次次的落榜中,临到两鬓似霜,飞雪满头时,一个转瞬即逝的“梦里功名”是否安慰得了己到强弩之末的身心?《文昭关》里东皋公一唱三叹:“将军为何白了髯?”《红楼梦》里有句曲词道:“气昂昂头戴簪缨,气昂昂头戴簪缨,光灿灿胸悬金印;威赫赫爵禄高登,威赫赫爵禄高登,昏惨惨黄泉路近。”如果曹松和陈俢们能有幸听到,不知会不会泫然流泪……
(三)
点额不成龙,归来伴凡鱼
太白有诗曰:
太白有诗曰:
黄河三尺鲤,本在孟津居。
点额不成龙,归来伴凡鱼。
荣耀也好,热闹也好,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事,科举考试的残酷性就在于它每次都制造出绝大多数的失败者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一部分人,便觉得天地异色。
白居易说:
把酒思闲事,春愁谁最深?
乞钱羁客面,落第举人心。
杜牧讲:
降虏将军思,穷秋远客情。
何人更憔悴,落第泣秦京。
“只恐双溪蚱蜢舟,载不动,许多愁。”这自然是少妇的春愁,但落第之愁较之却有过而无不及。明代的陆世明落第还乡,途中经过一地关卡时,却被误以为是贩货的客商,勒令纳税,陆世明当即题诗一首相赠道:
献策金门苦未收,归心日夜水东流。
扁舟载得愁千斛,闻说君王不税愁!
如今妾面羞君面
白首青衫犹未换,又骑羸马出函关。
陆世明落第后归心似箭,大概是和孟郊一样,家中有一位倚门倚闾、“意恐迟迟归”的慈母。而落第后的罗邺却不免大犯踌躇:
年年春色独怀羞,强向东归懒举头。
莫道还家便容易,人间多少事堪愁。
为什么说“莫道还家便容易”呢?清代曾国华的话可以作为一个精彩的注解。他于咸丰年间落第返家途中给大哥曾国藩写信道:“出门时,父母嘱望,私心期许,岂如此耶?至鲇鱼坝肉店,必须买一猪肚蒙面,然后可进里门也。”
罗隐肯定也是戚戚与此有同感的。这位著名的“晚唐三罗”之一,诗才甚俊,自视也极高,十余年前赴试路过钟陵时,巧遇长袖善舞的歌妓云英。“早岁哪知世事艰,中原北望气如山。”当时的罗隐也定如陆放翁般裘马轻狂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或许还曾学张生向莺莺夸下海口:“凭着胸中之才,视官如拾芥耳!”岂料“五湖烟月奈相违”,“十年心地仅成灰”,十年后故地重游,“云英抚掌曰:‘罗秀才犹未脱白耶?’”,罗隐惭恨入地,赋诗一首相嘲道:
钟陵醉别十余春,重见云英掌上身。
我未成名君未嫁,可能俱是不如人!
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钱起曾对一位金榜题名的朋友说:“借问还家何处好,玉人含笑下机迎。”衣锦还乡时,妻子兴高采烈地从织布机上跳下来,亲热地拉着自己的手问长问短,该是何等地温馨!而落第者便没有这个待遇,唐青臣回家时的情景是这样的:
不第远归来,妻子色不喜。
黄犬恰有情,当门卧摇尾。
说来唐青臣还不算最糟的,老婆只是横眉冷对而已,而且还有只黄狗对自己摇尾巴。杜羔的老婆干脆连这个机会都不给。唐德宗贞元年间,杜羔连续落榜多次,这次又要落魄而归了,妻子听说后马上寄来一首诗:
良人的的有奇才,何事年年被放回?
如今妾面羞君面,君若来时近夜来。
同学少年多不贱
“有情天地内,多感是诗人。”高兴时是“子规啼欲死,君故不知愁”,悲伤时却是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施肩吾落第时痛感“天遣春风领春色,不教分付与愁人”,登科后却又觉得“江神也世情,为我风色好”;那个人送雅号“赵倚楼”的赵嘏落第后再没有兴致去描摹“残星几点雁横塞,长笛一声人倚楼”的意境,而是“别到江头旧吟处,为将双泪问春风。”
“贫疑陋巷春偏少,贵想豪家月最明。”不同的境遇对比,往往更加重人们内心的感伤与失意。此正所谓“寂寞正相对,笙歌满四邻。”“傍人贺及第,独自却沾襟。”
“同学少年多不贱,五陵裘马自轻肥!”别的倒还罢了,当那些“齐入文场同苦战”的同窗好友金榜题名,而自己却名落孙山,此时更情何以堪!“几年辛苦与君同,得丧悲欢尽是空。”这是落第的温庭筠面对及第同窗时的凄苦心情;“得水蛟龙失水鱼,此心相对两何如?”这是落第的李山甫面对及第朋友时的尴尬处境;而最凄苦尴尬的莫过于唐人刘虚白,他二十年前与裴垣同窗共读,等裴垣及第多年后担任主考官时,刘虚白还是个应试举子。考试当天,刘虚白向昔日的同窗、今日的主考献诗一首:
二十年前此夜中,一般灯烛一般风。
不知岁月能多少,犹著麻衣待至公!
(四)
何事欲休休不得?
三年复三年,所望尽虚悬。
五夜闻鸡后,死灰复欲燃。
63岁的蒲松龄辗转难眠。
而他在《聊斋志异•王子安》中对秀才落榜后穷形尽相的描摹,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:
初失志心灰意败,大骂司衡无目,笔墨无灵,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;炬之不已,而碎踏之;踏之不已,而投之浊流。从此披发入山,面向石壁,再有以‘且夫’、‘尝谓’之文进我者,定当操戈逐之。无何日渐远,气渐平,技又渐痒,遂似破卵之鸠,只得衔木营巢,从新另抱矣。
刚落榜时大骂考官瞎眼,将笔墨纸砚尽数焚毁抛弃,并直欲披发入山,永绝尘念,此时再有谁给自己看应试文章,一定拿起刀来追杀他。可日子一长,又觉得技痒难耐,心有不甘,遂如“破卵之鸠”般“衔木营巢”,从头再来。
“何事欲休休不得?来年公道似今年!”韦庄也是这样地“看得破,忍不过”。“偶赋凌云偶倦飞”,那不过是轻薄子的玩笑罢了,柳永嘴上说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但皇帝真要他“奉旨填词”时,他还要不惜变了姓名去应试;卢纶曾经很滑稽地说:“谁怜苦志已三冬,却欲躬耕学老农!”诚然,十年寒窗辛苦用功,又有哪个愿意轻易将自己的“万字平戎策”,去“换取东家种树书”?
屡次落第的唐皋请人画了一幅《渔翁风雨图》,图中一位白发渔翁在连天风雨的湖中孤独地撒着网,他在图上题诗一首:
一网复一网,终有一网得。
笑杀无网人,临渊空叹息。
他就这样“一网复一网”地一直撒下去,直到五十八岁一网打到一个状元。
唐皋和曹松们都还算是幸运的,因为虽然撒网撒到两鬓如霜,总算是“终有一网得”,象唐皋还网到了一条大鱼。但那些撒了一辈子网连个虾米也没有捞到的呢?对他们而言,考试已经成了“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”的鸡肋,他们就象那个白发渔翁一样,在漫天风雨中,孤独地一网一网撒下去,直到自己也一头栽倒在湖里。
(五)
更望谁家门户飞?
朝向公卿说,暮向公卿说。
谁谓黄钟管,化为君子舌。
一说清嶰竹,二说变嶰谷。
三说四说时,寒花拆寒木!
孟郊说得何其激动人心!
在科举时代尤其是唐代,权贵名流的举荐对及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比如项斯投行卷给国子监祭酒杨敬之,得到杨的赏识,竟至于“到处逢人说项斯”;朱庆余投行卷给水部员外郎张籍,赢得张“一曲菱歌抵万金”的激赏,从而都立即声名大着,进士及第。杜牧献《阿房宫赋》于太学博士吴武陵,吴向主考官崔郾极力推荐,当即定下杜牧第五人及第;王维以妙解音律结识岐王,并由岐王引荐,以一曲《郁轮袍》打动了权倾朝野的安乐公主,夺得状元。这些优秀的范例给了落第者极大的鼓舞,他们悄悄拭去腮边的泪痕,精心整理好心血凝成的行卷,匆匆加入到谒见权贵名流的队列之中。
唐宪宗元和十三年,章孝标落第,他写了一首《归燕》诗,呈送该科主考官礼部侍郎庾承宣:
旧垒危巢泥已落,今年故向社前归。连云大厦无栖处,更望谁家门户飞?
“春回大地,我也从南方飞回来了,到家时却发现旧巢已毁,无处可归。长安城里高楼林立,却已无我的立锥之地。我眼望一家家门户,在料峭的春寒中徘徊翻飞。”
形象地描摹出自己凄惶失落的心情和孤苦无援的处境,让人似能听见他期待汲引的声声哀鸣。庾承宣反复展读,爱不释手,颇有遗贤之憾。刚好庾来年再任主考官,便毅然录取章孝标为进士。当时人们就认为章孝标“以二十八字致大科”,遂引发了又一个积极投行卷于权贵的高潮。
象章孝标那样凄凄哀鸣的还有郑谷,他落第后给柳玼写信道:
砌下芝兰新满径,门前桃李旧成荫。
却应回念江边草,放出春烟一寸心。
“你先前提拔了那么多门生,他们已如桃李郁郁葱葱;现在又奖掖了这么多后进,他们就象芝兰满庭满径。请你现在也可怜可怜我这棵寂寞生长在江边的小草吧,给它些许雨露,让它抽出嫩芽一寸寸。”
曹邺在落第后,说得更凄婉:
愿怜闺中女,晚嫁唯守节。
勿惜四座言,女巧难自说。
“这里有一个错过了婚假年龄但又很守规矩的好女孩儿,深闺如海啊,无以自明。希望你能怜惜她的一片苦心,别让她就这样埋没终生。”
杜荀鹤是一个自尊而敏感的诗人,谒见权贵时还要声明“非谒朱门谒孔门”,谒见同姓的名流时说是“吾宗不谒谒诗宗”,很有些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当又一次落第时,给一位做官的朋友写信说:
丹霄桂有枝,未折未为迟。
况是孤寒士,兼行苦涩诗。
杏园人醉日,关路独归时。
更卜深知意,将来拟荐谁?
“杏园人醉日,关路独归时。”从诗中可知,杜荀鹤在向那位朋友凄凄哀鸣之后,最终还是很落寞地回家了。但更多的人还是象杜甫一样“漂”在京城: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。……”
(六)
灞陵老将无功业
清康熙年间的马世琪是江南出了名的才子,做八股文的水平更是声闻一方。但在一次应试举人时,考了《渊渊其渊》这一试题。马世琪由于求胜心切,太想在试卷中尽展才华,反复掂量,不肯轻易落笔,直到临终场时,还没写一个字,等到别人纷纷退场,他也只好放弃,于是在试卷上题诗一首∶
《渊渊其渊》实难题,闷煞江南马世琪。
一本白卷交还你,状元归去马如飞。
自己交了白卷,考不上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虽然也可惜弄丢了状元,但还没有像张铁生那样,交了白卷还要硬着脖子说“不学ABC,也做接班人”。但高才落第如马世琪这样的只是一个特例,绝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。
有过切肤之痛的罗隐曾经痛切地指出,科举取士,“得之者或非常之人,失之者或非常之人。”即科举能网罗到优秀的人才,也能失去优秀的人才,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。即如罗隐自身而言,这位晚唐诗坛名家,一连考了十次都没有考中,后来只得投奔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做一名幕僚。“南来北去二三年,年去年来两鬓斑”,唐昭宗光化年间,罗隐已经垂垂老矣,同事将及第新榜拿给他看,罗隐不胜感慨,在榜后题诗一首:
黄土原边狡兔肥,矢如流电马如飞。
灞陵老将无功业,犹忆当时夜猎归。
自比百战而不得封侯的名将李广,寄予了自己无限的悲愤与惆怅。
古琴无俗韵,奏罢无人听
洪迈的《夷坚志》里说:北宋和州人杜默,累举不成名,一次落第后过乌江项羽庙,大醉后抱着泥像的脖子痛哭道:“大王,我们都太委屈啦,英雄如大王,而不能得天下;文章如杜默,而进取不得官!”杜默走后,庙祝看见霸王的泥像也洒泪不止。这个故事流播甚广,明人沈自征还把它演绎成著名的杂剧《霸秋亭》:楚项王泪湿泥人脸,杜秀才痛哭霸亭秋。
“文章如杜默,而进取不得官”,一个原因是主考官衡文水平太差,高才难遇知音。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:
古琴无俗韵,奏罢无人听。
寒松无妖花,枝下无人行。
落第后的孟郊说得更加直白而痛切:
离娄岂不明,子野岂不聪?
至宝非眼别,至音非耳通!
蒲松龄更是斥骂有些考官前生是“饿鬼道中游魂”,“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”,弄得心瞽而目盲。在唐代,更有瞎眼考官遭报应断子绝孙的传说。咸通、干符年间,李洞在礼部侍郎裴贽门下考了三次,三次落第。在第二次考试时曾赋诗道:“公道此时如不得,昭陵恸哭一生休。”意思是说我这次再录取不了,就到昭陵上哭太宗皇帝去(让人想起焦大要去祠堂哭老太爷去),然后再一死了之。李洞后来是终于潦倒而死了的,《唐摭言》说:“裴公无子,人谓屈洞之致也。”报应这种事本属渺茫,更何况后来还有人辛苦地考证出裴贽是有儿子的。人们编出这样的故事来,反映出的是一种激愤而又快意的复杂心情。
想来明末“江西四家”之一的陈大士是很了解这些瞎眼考官的,以制义时文名噪天下的他,却蹉跎场屋数十年,求一第而不能。相传他考到六十八岁那年,忽然大彻大悟,文章做毕,反复吟咏,叹息道:“如此文章,又有谁能欣赏得了呢?”于是重新做了一篇交卷。这篇应试文章与平时的习作相差甚远,但却如愿以偿地中了进士。
再如蔡元培。据野史记载,蔡元培于光绪十六年参加会试,考试结束后将文章副本呈送给乡试时的座师、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李文田。李文田看了之后叹息道:“你好不胡涂!这样的文章只有我能够赏识,你却把它写在会试的文章中!”吓得蔡元培不等会试发榜,便离京南下。
值得庆幸的是蔡元培最终还是被王颂蔚这样的伯乐发现和取中了,但李文田的叹息和陈大士的叹息一样,都流露出了对科举衡文无限的激愤与绝望。
(七)
不许平人折一枝
高才落第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录取过程中的种种黑幕。有人情关,如唐末诗人章碣。章碣乃章孝标之子,论诗才而言,似乎还是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如他题秦始皇焚书坑的名句“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,几关千古登临之口。但他的运气却远不如乃父。据说有那么一次,本有可能被录取,但主考官高湘却把这个名额送给了自己新收的弟子邵安石。于是落第的章碣写下了名为《东都望幸》的一首诗:
懒修珠翠上高台,眉月连娟恨不开。
纵使东巡也无益,君王自带美人来。
如果说章碣的言词还遵循着儒家诗词那温柔敦厚、怨而不怒的传统的话,胡曾则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胡曾出身寒苦,又生不逢时(晚唐诗人黄滔曾经指出:“咸通、干符之际,豪贵塞龙门之路,平人艺士,十攻九败”)。胡曾考了一年又一年,“年年模样一般般”,不由得一腔怒气冲霄汉:
翰苑何时休嫁女,文昌早晚罢生儿。
上林新桂年年发,不许平人折一枝!
“春卿拾才白日下,掷置黄金解龙马。”“闭户十年专笔砚,仰天无处认梯媒。”“九重城里无亲识,八百人中独姓施。”“晴天欲照盆难反,贫女如花镜不知。”孤寒者一字一泪,道出了心中无限的凄凉与无助。
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张居正。“一代名相、十年帝师”富国强兵的功绩自然彪炳史册,但他也干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,比如其次子张嗣修和第三子张懋修先后以榜眼和状元及第,便与他的授意不无关系。虽然事属暧昧,但已经大大激怒了无数出身寒苦的读书人,有人仿效唐代“无名子谤议”的方式,偷偷地在朝门上题诗一首:
状元榜眼姓俱张,未必文星照楚邦。
若是相公坚不去,六郎还作探花郎!
张居正死后,两个儿子都被革去功名,由于他们考中时分属万历丁丑科和庚辰科,所以当时人称“丁丑无眼,庚辰无头”。
不栽桃李种蔷薇
科场中的人情请托有时会恶化为对人才的恶意压制。唐文宗太和二年,刘蕡应制科,上对策万言,极言宦官之祸。其过人的胆识声震朝野,但当时宦官权势熏天,主考官自然不敢录取。即便如此,宦官头子仇士良还恼羞成怒责问刘蕡先前的座师杨嗣复:“你怎么胆敢将国家科名送给一个疯汉子呢?”而杨嗣复也只好恐惧地回答:“我过去录取刘蕡的时候,他还没有疯。”刘蕡“期月之间,屈声播于天下”,后虽曾被令狐楚、牛僧孺这样的显宦引入幕僚,但仍然没有逃脱贬窜极边,客死他乡的下场。而刘蕡对策之后七年,便有了宦官集团诛杀朝臣,胁迫皇帝的“甘露之变”。
“篱落荒凉僮仆饥,乐游原上住多时。”唐穆宗长庆年间的一个春天,贾岛又一次落第长安。据说落第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不好,而是先前写过“黄雀并鸢鸟,俱怀害尔情”之类的诗讥刺了当权者。此时的贾岛自然没有心思去琢磨到底应该是“僧推月下门”还是“僧敲月下门”,达官贵人们在城南新建了一座园林,正好去散散心。满园的春色自然是极美的,可贾岛目睹池水如碧,蔷薇似火,更觉得心赛油烹。于是毅然走笔在亭中题诗一首:
破却千家作一池,不栽桃李种蔷薇。
蔷薇花落秋风起,荆棘满园君始知!
贾岛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以著名的苦吟诗人著称于世的,曾自谓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但此诗却直抒胸臆,一气呵成;贾岛的诗歌往往追求清奇、冷峭的意境,与孟郊合称“郊寒岛瘦”,但这首落第诗却写得如此痛快淋漓,热血沸腾!乍读之下,我很奇怪一个清寒苦瘦的文弱书生竟能一下子变得如此地金刚怒目。正像在孟郊的诗集中很难再找到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这样的意气风发一样,在贾岛的诗集中,也很难寻觅到这种痛快淋漓。
贾岛好不容易“痛快淋漓”了一回,却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不久他就和平曾等十个爱发牢骚的举子一同被定为“举场十恶”,远远贬逐(开无官受贬之滑稽先例),从此注定了自己一生的凄凉。
外面无贵舅,家中无富婆
明代冯梦龙的《古今谈概》里有一则轶闻,对科场中考官为人情和金钱上下其手的黑幕作了综合的注解。当时浙江考秀才的府试,录取极难。如果没有“工夫在场外”,读尽诗书也是枉然。湖州府乌程县有一位考生,因为妻舅在朝中作大官,偷偷递了一张条子,不用说,被录取了;还有一位考生,把妻子的首饰簪环收拾卖掉,换了白花花的银子去打点,也捞到一个秀才。大概是做得不够机密,被大批的落第者侦知,于是有人做了如下一首打油诗道:
湖州有一舅,乌程添一秀。
舅与秀,人生怎能勾?
佳人头上金,才子头上巾。
金与巾,世间有几人?
外面无贵舅,家中无富婆。
舅与婆,命也如之何!
落第者偷偷地题诗一首,讽刺一番,大骂一通,也不过是徒然过过自己的嘴瘾。瞎眼考官不会因为有太多的高才落第便“另换一副眼睛肺肠”;而廉耻丧尽者的脸皮与心肠更早已修炼得是“厚而硬,黑而亮”,笑骂由汝,权贵依然照顾,银子照收不误。即便朝廷为此兴过大狱,开过杀戮,但被抓住的几率实在太小,正如洪迈所言,“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。”科场舞弊已经成了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,也成了无数贫寒士子一块无法绕过的绊脚石。
(八)
打鼓论榜
如果某科考试实在难服众口,落第者的反应自然会比写几首讽刺诗更激烈一些。在宋代,便有所谓的“打鼓论榜”。宋太宗端拱元年戊子科,礼部先是录取了二十八名进士,落第者叶齐击登闻鼓告御状,认为取士不公,一时物议哗然。于是宋太宗诏令复试,又补录了以叶齐为首的三十一名进士。有宋一代,对文人比较宽容,所以很有几次类似的“打鼓论榜”得到皇帝的支持,通过这种方式累计补录的进士竟有七、八百人之多,时人称之为“还魂秀才”。
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叶齐那样的好运气。明孝宗弘治年间,吴伯通督学浙江,府试时黜落过多,落第者上告至御史台。御史台责令吴伯通复试。吴大光其火,于是出了“鼋鼍蛟龙鱼鳖生焉”的怪题,外加策论“滚出来”。这样的题目不但语含侮辱,而且极难措辞,通过自然寥寥。有落第者便作诗叹道:
三年王制选英才,督学无名告柏台。
谁知又落吴公网,鱼鳖蛟龙滚出来。
还有更晦气的人在。据《容斋随笔》记载,就在叶齐打鼓论榜稍前不久的太平兴国年间,孟州人张雨光落第,大概是受到的刺激太大,喝醉了酒在当街叫骂,而且还语侵皇帝本人,惹得龙颜大怒,将张雨光处斩。落第不服又带来了杀身之祸,张雨光的遭遇委实令人同情。
科场逼反
人才无处出身,势必另有发泄。事态发展的最极端地步,陈登原先生称之为“科场逼反”(参见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)。“科场逼反”最早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黄巢。黄巢起义的主要原因自然是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,但黄巢本人造反的直接诱因则是科举落第,《资治通鉴》说他“举进士不第,遂为盗。”落第后的黄巢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不第后赋菊》:
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
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后来黄巢果然率铁甲百万杀进长安,杀得“华轩绣毂皆销散,甲第朱门无一半”,“内府烧为锦绣灰,天街踏尽公卿骨”。虽然黄巢最后败死狼虎谷,但煊赫一时的李唐王朝从此分崩离析,名存实亡,二十余年后便被黄巢先前的部将朱温取而代之。
当年李世民大力提倡科举的意图就是要使“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”,而且要“赚得英雄尽白头”,不料到了他的子孙手里,反而让秀才们操刀而起,这无论如何都是英武的李世民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。
宋继唐五代之后,似乎很认真地研究了这一严峻而尴尬的问题。他们将“科场逼反”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名额太少,“英雄”的漏网率太高。正如苏轼所言:“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,不知其将噬人。”于是采取两项措施:一、大大提高录取率,有时一科竟能录取六、七百人;二、创建进士特奏制度,即定期选取一些考了很多次(如15次以上)的老举子,特赐为进士,以使人人皆存觊觎之心,老死场屋而不悔。这样做了之后是否就杜绝了“科场逼反”呢?远远没有。张元便是宋代“科场逼反”最著名的例子。
张元,北宋华州人,为人倜傥任侠,蔡绦《西清诗话》称之为“华州狂士”,王定国《闻见近录》说他“每夜游山林,则吹铁笛而行,声闻数里,群盗皆避。”可见也属于“天下英雄”之流。他于宋仁宗天圣年间参加科举,本来会试已经合格,却在最后一关殿试中被刷了下来。大概这样的情况还经历了不止一次,于是张元便佯狂悲歌,托兴吟咏,曾写有豪情满怀的《雪》诗一首:
五丁仗剑决云霓,直取银河下帝畿。
战死玉龙三十万,败鳞风卷满天飞。
乍读此诗,便会深感其立意与语气和黄巢的《不第后赋菊》简直如出一辙!就是这个张元,后来与吴昊一起叛逃西夏,挑唆西夏主元昊兴兵抗宋,并亲自指挥“好水川之战”,使得宋军万余几乎全军覆没,并折任福等数十员大将,名将夏竦、韩琦、范仲淹也都因“好水川之败”而被贬官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:宋夏“连兵十余年,西方至为疲敝,职此二人为之也。”
殿试黜落,怨归人主;科举本为取士,反资之敌国。这些都是与统治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的,所以亟须找到相应的对策。据王栐在《燕翼诒谋录》中讲,后来的殿试只定名次,不再黜落,便是因张元叛逃之事而起。此后这一制度历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,伴随着整个科举制度直至其寿终正寝。
科场逼反还在继续。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时,湖南衡山人洪大全也起而响应。他在被俘之后的自述中说自己“自幼读书作文,屡次应试,试官不识我文字,屈我之才。我就当和尚,还俗以后,又考过一次,仍未取进。我心中愤恨,遂饱看兵书,欲图大事。”寥寥数语,将一个怀才不遇、求进无门,终于被逼上梁山的落第读书人的形象勾画得血肉丰满。
科举从最初的“英雄豪杰,汨没其中而不自觉”,“老死文场亦无所恨”,沦落到最终的“科场逼反”,这是无数良法美政在执行过程中都跳不出怪圈,还是历史所开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?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还在于,当坚船利炮从海上隆隆开过来时,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危险的威胁,已经不再是本国不安分的“英雄豪杰”,而是那些处于“王化之外”的“犬戎”、“夷狄”。科举已经担负不起自己的使命,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科举……
(九)
不向东风怨未开
王安石在劝勉一位落第的朋友时说:“意气未直轻感慨,文章尤忌数悲哀。”毛泽东也曾说过:“牢骚太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”自然也有一些人,面对落第,甚至不公平的落第,心态较为平和,心胸较为旷达。唐代的高蟾便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。五代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称他“守寒素之分,无躁竞之心”;元代辛文房的《唐才子传》称他“性倜傥离群,稍尚气节”,“其胸次磊块诗酒能为消破耳”。他的落第诗这样写道:
天上碧桃和露种,日边红杏倚云栽。
芙蓉生在秋江上,不向东风怨未开。
“新进士们恰似天上的碧桃与日边的红杏,得雨露滋润,生得郁郁葱葱,开得姹紫嫣红;而我就像那寂寞生长在秋江里的芙蓉,虽然不能绽开花朵,却也并不抱怨没有吹来东风。”
高蟾的诗写得余音袅袅、含蓄隽永,而清代李调元的落第诗却显得平实而坚定:
世上怜才休恨少,平生失学本来多。
天公有意君知否?大器先须小折磨。
而落第诗到了唐伯虎那里,则给人一种直白的放达。这位一代风流才子,乡试时高中解元,却在会试时卷入暧昧的科场舞弊案,断送掉似锦的前程。从此寄情诗酒,放浪形骸,以卖画为生,仍不废啸傲:
领解皇都第一名,猖披归卧旧茅蘅。
立锥莫笑无余地,万里江山笔下生。
不炼金丹不坐禅,不为商贾不耕田。
闲来写就青山卖,不使人间造孽钱。
有时把酒对月,放达之势直掩太白而上:
我也不登天子船,我也不上长安眠。
姑苏城外一茅屋,万树梅花月满天。
清代的赵翼论诗说: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是说在山河破碎,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,往往能催发出一些优秀的诗词篇章。而对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,科举几乎是他们唯一的进身之阶,得中与否也几乎等同于一场沧桑巨变。由此所产生的及第诗与落第诗,也便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透过这道风景,我们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一大群人,他们或肥马轻裘,或衣衫褴褛,或志得意满,或垂头丧气。我们看不清他们的面容,但可以触摸到他们的脉搏,感受到他们的呼吸,并能和他们一起看潮起潮落,大江东去。这一群人,曾经是这方蓝天下最活跃、最引人注目的一群,如今却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记忆……
返 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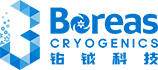

 沪公网安备 31011402009347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402009347号